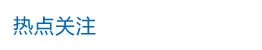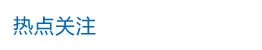z7x北京交通大学新闻网
所谓“伊人”,在我看来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最富文人风骨的意象。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中便已经出现了“伊人”的意象。而且我认为,自《诗经》诞生的商周春秋时期起直至今日,作品中对“伊人”咏唱的艺术效果及文化影响,还是首推《诗经》中的滥觞佳作《国风·蒹葭》。至乎《楚辞》中的《离骚》、《九章》还有《九歌》中部分歌咏鬼神情爱的篇章,更是通篇难忘“伊人”倩影。
所谓“伊人”,不可不细细品味。
读《蒹葭》,发现伊人总是在水一方。“我”,抒情者,溯洄寻觅,却总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从希望到失望,再到重拾信心,继续跋山涉水,承受着一次一次的痛苦;然而“我”却可以永不放弃,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经过一夜复生,重以完整的人格姿态面对翌日的曙光。在歌咏“伊人”的同时,“我”也一直在浅吟慢酌地诉说自己的故事;“伊人”与“我”,咋看去姿态上的区别是一高一低,其实却是 “伊人”因“我”的期待而被寄托了“我”的精神风骨,“我”因“伊人”而拥有了独立的人格气质,恰似板桥笔下劲竹,又若夫子所赞松柏,耐得住困苦风霜,经得住坎坷险阻,任尔东西南北风。
可以说,“伊人”即“我”所力臻的自我;二者在空间高度上牧马牛不相及,却在精神层次上又臻至匹配、统一。“伊人”是虚,“我”是实;所谓“伊人”,若是真正超越了虚实的界限,终究看到的是“我”。
读《离骚》,则感到“伊人”与“我”的空间距离更似人神相隔。在《离骚》中,“伊人”代表了屈大夫毕生所守护的楚国大业,或为行即迟暮的美人,或为婀娜奇美的山鬼。《楚辞》既被誉为中国古典诗词浪漫主义诗歌之源,与代表现实主义诗歌之源的《诗经》相较而言,其艺术感染力更趋饱满、深沉。且看屈大夫天上一句,人间一句,句句莫不是在向“伊人”倾诉“我”的心事,“我”的喜、怒、哀、乐,“我”的嗔、痴、怨、恋。叹唱罢了,总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抱负,总还是无法忘怀“伊人”,以至于衣带渐宽,形容枯槁。有如《湘夫人》所咏:“帝子降兮北渚,目邈邈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此刻仿若人神相隔,天上人间,“伊人”终究难以追及挽留。悲夫,斯情也!
另一方面,种种困苦也衬托了“我”的坚定执着,“我”的壮志傲骨,哪怕世人皆非,也依旧睥睨浊污,横流独往矣!
须知屈大夫之后,还有蔺相如、诸葛孔明、苏东坡等有此千古风骨。他们或功绩千古、声名显赫,或时运不济、英雄泪襟;但无论静躁进退,他们无疑都组成了中华民族脊梁的一部分,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伟大。
所谓“伊人”,读懂了便读出了文人风骨。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离骚》笔记,仅四言,供大方见笑:
泪满襟兮酒入肠,衣拭剑兮寒月光。
扶不周兮矫日月,溉黄河兮治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