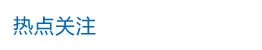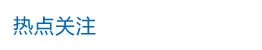高中时读过《鼠疫》,当时没什么体会,只觉得是一本描述人们遇到鼠疫时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的书。如今细细品来,反倒有种又闻已是曲中人的感觉。人们在鼠疫中的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表现出对幸福和安宁的渴望。鼠疫既可以是鼠疫,又可以是战乱,还可以是人们的痛苦。面对荒诞,如果人始终停留在这个阶段不做努力,人们的处境将会十分被动,而痛苦的状态却无法改变,但反抗是作出行动,用实际行动对“恶”的表现形式和荒诞进行反抗,结束这种状态。在反抗中,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出路,结束了痛苦,证实了人存在的价值。
一、荒诞
加缪创作过“荒诞三部曲”,其哲学思考也常被人认为是荒诞之思。加缪笔下的荒诞不是一种客观的荒诞,而是人的一种生存感受和主观体验,与人的生存有关,指的是一种荒诞感。这种荒诞思想探讨的是个体的生命和死亡,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他把荒诞哲学上升到人生高度。《鼠疫》中的“鼠疫”本就是荒诞的表现,1940年德国法西斯占领巴黎,城内的人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很多人认为文中的鼠疫就是这场战争,在我的理解中,“鼠疫”不仅是指战争,而是人本身的语言和行为的荒诞。加缪自己说过“《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
作者借塔鲁的视角讨论过对鼠疫的看法,塔鲁本身是一个专注于观察人们行为并善于将其记录下来的人,在第24章他同里厄医生“共述友情”说:“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十七岁的他旁听完父亲对犯人的一场审判,看到父亲说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这时候他在思考为什么父亲可以以社会的名义“谋杀”犯人,他认为这是以见证谋杀认同谋杀来消灭谋杀。接着他说:“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他认为这是以认同鼠疫的方式来促成鼠疫的传播,是人的行为导致的鼠疫,也就是这种荒诞的产生,而他意识到了。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书中大篇幅的描绘鼠疫中的奥兰城人们的行为,在鼠疫发生之前,他们起早贪黑工作,消磨时间,尽情纵欲。鼠疫发生之后他们为自己的习惯受到破坏而恼火,但又束手无策甚至任疫情宰割,亲情和爱情在疫情中被放大,“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他们感到自己被流放,空虚,我认为这是人们在感受鼠疫所带来的身体所受的痛苦时同时会感受的精神的痛苦,漫漫无期的疫情,你不知道自己会和爱人分离多久,但你却清楚完全有可能会变成永远分离。人们每天都出于被疫情压迫下的行为上的麻木和心理的痛苦中。当疫情结束时,“当他们一看到火车的浓烟,那种流放的心情 就在一阵使人忘乎所以的兴高采烈之中突然化为乌有了…里厄发现在行人的一张张脸上都带有一种亲如一家的神色……但这团聚的对象却是一种他们无法确定的东西,不过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合乎愿望的东西。因为想不出恰当的名字,有时,他们就把这东西称做‘安宁’。”这是和鼠疫中人们的行为所做的对比,人们的荒诞归于平静。
鼠疫中的科塔尔因为担心监禁而终日惶惶,“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科塔尔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在鼠疫中受到好处,感到自在,与荒诞融为一体,他直到鼠疫结束,开枪射击无辜人民,自始自终也没有走出荒诞。但是他恰如其分的了解奥兰人的思想正是因为他早已深陷泥潭,因为他在疫情前就知道自己将走向孤独,恐惧,对他而言,和别人一起分担恐惧比自己一个人恐惧要好点的多。这是人们的惯常想法,幸好还有别人跟我一样,这个过程中痛苦和焦虑是大家共同承担,并不单单存在于个人身上。里厄却不可能这样,因为他每天看到死亡,分离的痛苦,他看到纯洁无辜的孩子的因为鼠疫死去,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因为孩子的无辜衬托了鼠疫的恶,为什么要接受呢?为什么不反抗?
二、反抗
在加缪看来,当人类的尊严、爱、正义以及人格的完整性被否定时,便出现了反抗。在《鼠疫》中,里厄医生见证了反抗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由个人反抗转向集体反抗从而走向安宁的。从一开始里厄同里夏尔的辩论坚持政府要采取最严谨的措施,到后来大家一起加入抗击疫情的工作,再到最终所有人都走出自己的流放状态,拥抱他人,这整个一个过程回答了反抗是为了什么。期间的过程可以看到反抗也会带来痛苦,离别的痛苦,目睹死亡的痛苦,正因为过程如此痛苦,所以人们才无法逃避反抗,直到人生终点获得安宁这种反抗可能才会结束。
在这场鼠疫中,朗贝尔这个“异乡人”反抗与心爱女子分离的痛苦,用尽全力找出城的门路,却在即将出城的时候放弃了,“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在接触鼠疫工作后,他逐渐从一个外乡人的身份转变成了“这城里的”,他知道这件事是无法逃避的,与“我们”都有关系,反抗是“我们”一起的反抗。
这个“我们”在帕纳卢第二次布道时的细节也可以看到:“神甫用一种比第一次讲道时更加柔和、更加深思熟虑的语调说话,而教徒们有好几次发现他说话时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说话中已不称‘你们’而称‘我们’。”第一次布道时他未看过什么生死,将疫情只归结与神的指示,希望别人顺从天主的安排,但在经历了无辜孩子的死的事件之后,在面对医生的斥责“这个孩子至少是纯洁无罪的,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不,神甫。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时他悲伤的回答到:“我刚懂得什么叫天主的恩惠。”那时,他明白了天主也不能将“我们”分开,而事实上“我们”能反抗。他明白了他要告诉别人要反抗,他清醒而又迷茫,私下里他写《一个神甫能否请医生看病?》但最终临死前他也没选择医生治病。这是他的选择,他说:“但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他是矛盾的,最终的选择只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但他也难以承受不反抗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在我看来他没有选择找医生是自杀,他不允许自己有同天主斗争的想法,所以宁可随信仰去死。
格朗看起来是个普通的小人物,但事实上他又是一个反抗英雄。他普普通通的工作,有着一个“让人脱帽”的理想,还有一个畏首畏尾的性格和并不特别出色的能力。他在病床上发着高烧还要坚持梦想,改稿子,想着宽慰离去的妻子,但就是这个身体并不强壮的男人,最终反抗过了疾病。格朗就是我们普通的大多数,可能有一个想要受人尊敬的梦想,奈何能力平平。但在成功反抗鼠疫的过程中少不了这些人的兢兢业业,普通但从不平凡,就像现在在为肺炎疫情努力的所有人,是因为所有人一同的努力才会有最终疫情的结束。
塔鲁从他17岁旁听的那场审判起,就已经开始了反抗,反抗看到“谋杀”,接受“谋杀”。他反对任何形式剥夺别人的生命,他始终坚持站在受害者身边。他热衷观察,充满好奇和热情。在疫情中,她主动帮助里厄寻找人手推进战疫工作,即使辛苦也从未停下同别人的沟通。在他弥留之际,他也没有停止斗争“塔鲁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跟瘟神战斗着。整整一夜,在病魔的袭击下,他始终没有焦躁不安,而只是以他那粗壮的躯体和他那默默无声的意志力来进行斗争。整整一夜,他也从来没有吭过一声,他以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正全神贯注于斗争,不能有一刻分心……不过在他变得僵硬的脸上,两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闪耀着勇敢的光芒。”他就像一位勇士,永不疲倦,充满爱心,而死亡对于他来说也是斗争的结束,他得以永远安宁。
“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里厄医生在和塔鲁的谈话中这样说道,他对英雄和圣人都不感兴趣,但其行为已然像个英雄。塔鲁曾对他描述到:“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因为理性,所以胸有成竹。在没人敢确诊鼠疫时,他据理力争,在每日见证死亡,见证分离时痛苦却不愿气馁,在见不到自己妻子而伤心也不抱怨,在朗贝尔说他不懂分别之痛时他也不争辩。他拥有理性,智慧,同情心和责任心。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什么,我想就是反抗的人,他说他看不惯死亡,所以他就成为一名医生,反抗死亡。或许别人眼中的英雄,神都不属于他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里只有人,当你反抗你才有可能获得,永远无法寄希望于别人。
三、人生意义
朗贝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明明任何事都不值得舍弃所爱,那我为什么舍弃了呢?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加缪说过:“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你永远不会生活”。可能朗贝尔舍弃爱情的时候也并没有想到什么意义,只是见不得眼前的痛苦,他明白了一个人的幸福毫无意义。
在里厄和塔鲁谈心的最后塔鲁说:“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到防波堤上去。总而言之,要是只生活在鼠疫的环境中,那就太愚蠢了。当然,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不过,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反抗的过程不应该抛弃自己的心中所爱,不该抛弃心中所信,不然一切将毫无意义。斗争是因为痛苦太痛苦还是因为有希望可以不痛苦?书中多次提到血清,我认为血清就代表希望,里厄医生始终都对这个血清抱有希望,对将这种荒诞回归安宁抱有希望。或许这就是他的真正的人的意义。
“至于这种流放和这种团聚的愿望究竟有什么意义,里厄却又无从知晓。他继续往前走,到处人们挤他,向他吆喝。就这样,他渐渐地走到了行人比较稀少的街道上。他认为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都无关紧要,只须看到有这种符合人们心愿的东西存在就够了”在《鼠疫》文末加缪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于意义的观点,或许有没有意义无关紧要,或许灾难,痛苦,荒诞本就无意义也要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