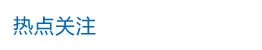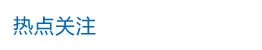一、果园城中的悲剧人物
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他借用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乡村小城人们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可以说,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果园城记》的灵魂。在这些人物中,除了像“魁爷”这样的果园城的统治者和像“小渔夫”一样乐天知命的纯朴少年之外,还存在着一系列的悲剧人物,他们或妥协、或挣扎,但最终都扑倒在命运的尘埃里,泯然众人。
第一,被遗弃者,代表人物有孟林太太、徐大娘、徐大爷。他们躲在时光的深处安静地活着,不与外界接触,他们的生活是沉寂的,他们机械地按照惯性度过时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丧失了生命的活性和存在的意义。
比如孟林太太,作者在描写孟林太太的居所时,反复运用了诸如“沉重”、“阴影”、“沉寂”、“神秘”等暗色调的词汇,而孟林太太本人也失去了以前的“端肃、严正、灵敏”,失去了“一种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少的精神”,甚至由着自己的心意,不让女儿素姑出嫁,拉着她同样消沉在沉寂的时光中。她在与马叔敖的谈话中,也显露了她的茫然和无意识的生存状态,在谈话中,她总是显露出一种不自觉的游离,时而表现出“失措的瞠然”,时而又变得“委顿”、“茫然”。
而对于徐大娘和徐大爷来说,他们生活意义的丧失来源于对他们儿子的爱。这种爱带给了他们生命的一切,相反,当徐立刚死去时,一切的希望和意义都被那种沉滞的伤痛剥离,他们的生命便由此停滞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大娘总是让人念她儿子的来信,甚至在吃饭时还放上她儿子的碗筷。
他们的这种遗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本身所造成的,他们在命运的折磨中渐渐妥协了,要不麻木了,要不便躲在记忆的罅隙中哭泣。
第二,漂泊无依的游子,代表人物有徐立刚、孟安卿。他们有抱负,有理想,讨厌果园城的平稳而又有些陈旧的生活。但在漂泊之后,却又产生无尽的迷茫。
他们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而走出果园城,但最后,他们在四处飘荡、身心疲惫之后,还是选择再一次回到果园城,但他们再也找不到那种心灵的归宿感。就像孟安卿一样,当他再次选择回到故乡时,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变化,一切好像都是老样子,但一切都似乎又排斥着自己,和自己的记忆格格不入,甚至连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样子也和自己想象的不同。所以他在惶恐中逃离了,所有的希望和期待都在一个转身中破碎。其实,他原本就什么也找不到,他所找寻的东西早就随着自己的往昔在时光中湮灭了,那是一种心灵上的归宿和慰藉,而并不单单只是一座果园城。
第三,失败的反抗者,代表人物有贺文龙、油三妹。他们不甘心现在的生活,倔强反叛,但最终被果园城那种亘古不变的生活所磨平,变得沉沦。
像贺文龙,他原本想成为一个大学生,后受时代所迫,只能成为一个小学教师。在师陀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果园城小学教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早晨,连最小最贪睡的学生都到学校里来了,他们从床上起来,喊校工打洗脸水,然后,吸烟…连主要的大街都显出疲倦,教师们要打哈欠了,照例下几盘棋,罚几个自己不喜欢的学生”。在这种无聊的生活中,贺文龙决定成为一个作家,这种“既不用资本也不必冒险的事业”。但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计划一再搁浅,最终,当他在他儿子手中再次发现自己的文稿时,他释然了,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希望,聪明,忍耐,意志”。或许,他“至今而后永不会想到它了”。
而这种人物的另一个命运是死亡,像油三妹一样。她在面对和贺文龙同样的命运时,先是有些痴狂了——“她喜欢自己或别人大笑,喜欢各种热闹,她所害怕的只有一样,好像故事里所说的害怕自己影子似的害怕孤独”,她的性子比贺文龙来得浓烈,所以她的反抗也显得那么张扬。最后,她还是被生活打败了,在一次喝醉后被国民党特务强奸了,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和可能随之而来的指指点点,油三妹自杀了。她的反抗也是悲剧的,她在反抗中被现实一次又一次打败,最后她只能选择死亡,一种类似妥协的又或许是最激烈的反抗。
这类人的命运大都如此,像作者所说“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少女,第一个将痛苦的去过完她的一生,第二个吃了藤黄,第三个,我也想收起我的颜料盒,我们何必描画这些痛苦的画像呢”。或许,对于这些只能囿于果园城而无法走出去的小人物来说,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四、一成不变的手艺人,代表人物有说书人、卖煤油的。在他们身上,似乎最能看到果园城的缩影——一成不变,似乎永远活在昨天。像邮差先生,他知道所有写信人的地址,甚至“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从这一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果园城生活的恒定,而这些人由于特殊的职业,他们的生命节奏是和果园城息息相关的,因此也变得沉稳而平静。同时,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又能看到那种带有生活气息的善良和一种略带凄凉的命运。像卖煤油的虽然抱怨着煤油的涨价,但同时,也可以“笑着叹口气”,同意别人的记账,这种场面无疑是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的,在这种生活气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宗法制乡土社会中特有的善良。
而从说书人死去的命运中——“就在这里,他们在这些永不会有人来祭扫,人家把他们埋葬后便永远将他们遗忘掉的荒冢中间掘了个坑,然后把说书人噶下去,将泥土送下去”,在这种冷漠和遗忘中,透露出了果园城人这种生时默默无闻,死后被遗忘的宿命,同时这种宿命也正是果园城的宿命。
二、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
在对上面四类人进行描述和总结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隐藏在他们悲剧命运之后的共同点,那就是时间。无论是反抗者、妥协者还是生存者,他们的命运都在时间的摆弄下变得支离破碎——时间改变着一切,人们面对时间的洗礼却无能为力。对于那些生存在果园城里的人来说,时间似乎永远静滞着那里。这种静滞是令人绝望,无论你怎样去反抗、去逃避,你永远无法改变身边的一切。就像小说中大刘姐所说的那样:“人无尽无休地吵着、嚷着、哭着、笑着、满腹机械地计划着,等到他们忽然睁开眼睛,发觉面临着那个铁面无私的时间,他们多么渺小、空虚、可怜,他们自己多无力呀”。而对于那些出走者来说,时间却又扮演着改变者的角色。一方面,在时间的洗礼下,他们渐渐成长、老去、改变,甚至失去了初心和那份寻找初心的勇气。另一方面,当他们为了逃避时间的改变,渴望回到果园城寻找一丝安慰的时候,面对的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果园城变了,同时也遗弃了他们。在《狩猎》的最后,孟安卿看到这失落的一切后,这样感慨着“他突然间感到兴亡变迁,时间加到人身上的变化。他想起他在旅馆里拔掉的白头发,无论如何修饰。他的终究无可遮掩的皱纹”。此时的他们是迷茫的,那是一种生命的悲剧——似乎再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那一刻,他们变成了真正的漂泊者,他们悲剧的命运就这样任由时间冲刷着。
而在时间之下,是现实的无奈。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清政府被推翻,国民党、共产党、军阀等各色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的果园城是无力改变的,他们一方面受制于统治者的频繁更换,封建势力根本不能根除,另一方面又受地理因素的限制。随着火车站——现代文明的代表的渐渐兴盛,自然而然地便被遗忘了。对于果园城中的人物来说,不反抗就只能被遗忘。而反抗呢,似乎更是悲剧。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一群有着种种陋习的村民,他们的反抗注定要失败。他们没办法冲破现实和观念的封锁,也没办法得到任何人的认同和帮助,他们的挣扎,只能是让自己的命运变得更为凄惨。像油三妹,还不如选择如同贺文龙一般的生活,妥协,但不至于丢掉性命。走出果园城的那些反抗者,他们的命运同样是悲剧的,因为在那个如此混乱的时代下,人的生命和理想原本就不值一钱,他们走出他们本身的命运和果园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果园城,他们根本就没法生存。这种自身条件的限制,注定他们没有能力去面对时光和现实中所衍生出的种种无常。此外,他们中的另外一部分人曾经接触过外面的世界,他们拥有新思想,他们渴望改变。但是他们本身的力量太过弱小,弱小到连在“新世界”里扎根都异常艰难,更不必说改变和反抗。同时这一部分人也是迷茫的,他们确实接受到了新思想,但是这种新思想只是给了他们改变的冲击,却不能为他们的改变提供动力——他们根本不能很好地消化这些新东西。所以,他们只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他们对于自己之后的人生并没有很好、很明确、切实可行的计划。在这种迷茫和弱小的限制下,他们失败的悲惨命运在所难免。然后,他们由“博学多识”所赋予他们的敏感情绪又会促进他们去思考,就像《颜料盒》中的马叔敖一样:“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应该幸福的人,他们曾经给人类希望,正是使世界不断生长起来,使世界更加美丽,更加应该赞美的他们,为什么他们要遭到种种不幸,难道是因为在我们的感情中会觉得更公平些吗?我们被苦痛和沉默压着。从上游,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愤激的、痛苦的、沉重的响着,好像在订棺材钉”。这种毫无作用而又充满伤信的思考,无疑使得他们更加迷茫和痛苦,这也是他们无法逃脱的死循环之一吧。
这种种无法逃脱的命运悲剧,或许就是跳出家乡的师陀对自己的家乡、甚至是对中国最广大农村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命运最深沉的思考。这种思考是迷茫的,师陀就像自己笔下的马叔敖一样,他知道这种思考是徒劳的,他知道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但这种思考和探索也是必然的——因为那份热爱和责任,因为对未来的希望。换句话说,这或许也是那代人、甚至整个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当然,师陀也给了我们面对这种绝望命运的方法“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有时候不绝望,或许已经是最大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