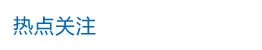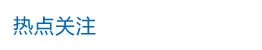刘建坤在青藏铁路沿线的风火山隧道调研。风火山隧道位于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边缘,全长1338米,轨道面海拔4905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
刘建坤,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5年出生,1986年获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学士学位,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工程冻土学工学硕士学位,后赴前苏联罗斯托夫建工学院进修工程地质专业,1994年获莫斯科建筑大学岩土力学专业博士学位,1995年回国。
异域求学不悔初衷
在冻土研究的道路上,刘建坤属于“半路出家”。
1986年,大学毕业的刘建坤来到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继续深造。由于本科所学并非冻土专业,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并由于外语成绩突出,被选中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
到莫斯科后,刘建坤与其他2名同学被分配到罗斯托夫——那个因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而被中国人熟知的城市。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难题——语言不通。
是时,学校安排刘建坤与另外2名外国留学生一起上语言课,可是一节课下来,他只听懂了老师说的“吃饭”一个词。无奈之下,校方为刘建坤单独安排了一个老师,每天4小时一对一授课。
回想起那段时光,刘建坤笑言:“当时我特别害怕那个老师,但是也正因为害怕,就这么学出来了。”
无法开口说话的痛苦让刘建坤自创了一套提高俄语水平的学习方法。从宿舍到学校之间的五六站距离,成为他学习的天然课堂——商店里的货物标签就是“单词卡”,店主与客人的对话成了最好的“听力材料”。回到宿舍,刘建坤都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地新闻,一边听一边阅读在路上买来的报纸。刚开始时,他几乎要把所有单词都查一遍才能理解意思,但是慢慢地,语言就不再是困扰他的大难题了。
由于罗斯托夫地处前苏联南部,没有天然存在的冻土,在罗斯托夫学习1年后,刘建坤去了莫斯科建筑大学。在那里,他体验到了与国内学习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氛围。
“‘自律’是我在莫斯科建筑大学最大的感受。”刘建坤说,“那里的学习完全靠自觉,如果不抓紧,很多人都拿不到学位,即使拿到了学位也不敢从事专业工作。”
在这样一片自律的氛围中,刘建坤经过几年的刻苦攻读,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虽然当时不少同期留学生在社会浪潮中选择了从商、移民,但刘建坤还是信守自己当初的留学初衷,回到国内并在北京交通大学申请到教职,专心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
两赴青藏 筑梦高原
1999年,刚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香港科技大学访学归来的刘建坤,正赶上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开始修建,刘建坤便参与到了其中有关路基建设的课题攻关中,并由此开始了真正的科研之路。而这之后的青藏铁路建设,则成为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骄傲。
所谓冻土,是指0℃以下,含有地下冰的岩石和土壤。由于冻土对温度极为敏感,随着温度变化,其体积会发生剧烈胀缩,从而破坏路基和路面。因此在冻土层施工难度极大。事实上,早在近百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构想过修建青藏铁路,但高原的冻土一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那么,青藏高原冻土区冻胀度到底有多少?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怎样?又有哪些具体问题亟待解决?
带着这些问题,刘建坤早在1996年底便主动联系到海拔4400米高的青藏高原东部214国道花石峡野外冻土观测站驻扎,不要求任何待遇,也不领取工资,只为科研取得第一手资料。
花石峡野外冻土观测站条件简陋,只有一栋简单的平房,挑水要到几百米外的小溪,与刘建坤相伴的只有一位负责做饭的师傅。他们和外界的通信,只能靠一个无线电台。“一周才能与省会西宁联系一次,每一次联系都要单独发电,也不一定联的通。”刘建坤回忆说,“而且那时候交通不便,从西宁到花石峡,开车单程要9个小时,路况非常差。”
正是这段艰苦和寂寞的时光,让刘建坤完成了对多年冻土段214国道路基的温度、变形的观测和病害调查,对该线多年冻土内的路段进行了全面考察,也因此参加了交通部盐湖路基加固方法的研究课题。该课题后来获得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001年,青藏铁路终于要上马了,这对我国从事冻土研究的科学家们来说是一生难求的机遇。由于我国很少在高寒、高原地带修筑高等级铁路,冻土铺轨专家奇缺,而作为国内少数拥有交叉学科背景的专家,刘建坤再次踏上了这片他熟悉的高原。
面对青藏高原冻土区沉降的难题,刘建坤领导团队经过艰苦的探索,最终选用冷冻地基的办法。“我们向冻土层打入充满液氮等制冷剂的冷冻管,让冻土在夏天不会融沉,保障沉降在安全范围内。”刘建坤说。
大原则解决了,小问题却不断出现。冻土区的路桥连接处,路基筑在土壤上,经常会随着温度变化而起伏不定。而铁路桥则由钢筋混凝土筑成,沉降幅度很小。由于路基、铁轨高度发生了变化,火车通过路桥连接处时十分危险。
经过几个月的观测,刘建坤发现冻土区很多大石堆下的冻土总是保持形态不变。经过反复的实验验证,他找到了原因:“石块挡住了阳光带来的热辐射,高原上冰冷刺骨的风却能穿过石头间的空隙吹倒土壤上,这就相当于天然冰箱,将冻土保护了起来。”
后来,刘建坤带领团队做好模型,让工程人员在靠近桥台的地方由大到小铺满碎石,模拟天然石堆保护冻土的形态,路桥连接处沉降不均的问题迎刃而解。刘建坤说:“看着合格的施工检测结果,便觉得几个月的冻没白挨。”
勤于授业桃李不言
作为一名教师,刘建坤的“战场”除了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还有咫尺之遥的三尺讲台。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崛起,依赖于许多因素,其中关键的因素便是人才。我国冰川冻土研究比国外起步晚,要想实现学科发展,最离不开的是对人才的培养。事实上,这也是促使刘建坤回国后选择在北京交通大学任教的主要原因。从1996年执教至今,刘建坤在这片“战场”上,同样“战果颇丰”。
采访中,刘建坤的一位研究生表示,读研之前他有一种担忧,怕不知道自己在这几年中到底能学到什么。他说:“虽然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万一师傅不给我领进门可怎么办?”
如今,这位学生很幸运自己能成为刘建坤的学生:“研一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跟着学长们打基础,到了研二就根据自己擅长的方向做深入研究。班里别的同学还在寻找研究方向的时候,我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一些成绩了。刘教授总说,学生的时间也很宝贵,不能浪费在帮导师做一些打杂的事情上面。”
刘建坤的实验室位于北京交通大学校园东北角的一座小楼里,看似最不起眼的地方,却是他与学生们一同努力的天地。路基实验不但辛苦而且繁重,有时候因为器械巨大,一两个人根本无法操作,一天试验下来,学生们都是灰头土脸,但是谁也不觉得辛苦。
研究生于钱米告诉笔者:“成天跟土打交道,能不脏嘛?可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都很开心,因为刘老师从来不给我们压力,而且我们也不把这当成是任务,我们是乐在其中。”在这里,刘建坤和学生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国家级重点项目,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
路基工程实验需要大量的器材和设备,刘建坤也从来不吝惜这方面的投入,实验室的很多仪器,都是他自己花钱买来给学生们用的,比如大型动三轴仪、大型直剪仪,很多仪器都价格不菲。他说:“做教师一定要有积累,要清楚买哪些器材给学生做实验,课题才能做得深入,后面的学生也才能继续下去。”不但如此,刘建坤还鼓励学生自行研发实验设备,自己建立低温室,很多学生开发的便捷仪器都被运用到具体的实验当中。
说到刘建坤的实验室,不得不提的便是每周1次的例会制度。每周五,他都会和学生们坐在一起,了解项目进度,分析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除此之外,刘建坤还会在例会上向学生们介绍最新的国际前沿科技,探讨目前国内国际最先进的技术。他的学生笑谈,自己最怕开例会,因为怕自己的进度赶不上别人拖后腿,但是也最喜欢开例会,因为总是能学到许多新知识。
转瞬间,一趟趟列车已经在青藏高原上飞驰了近10个年头,那段与高原冻土的较量经历也已经慢慢成为刘建坤生命中的一段过去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挑战冻土的脚步就此停驻。随着我国铁路建设的不断迈进,涉及冻土领域的研究课题也越来越多。如今,刘建坤和他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冻土吸水和膨胀研究这一国际尖端课题。
“冻土虽是小众的研究范畴,但却够我们研究上一辈子了。”刘建坤说。
http://www.chisa.edu.cn/szxrzz/qikan/2014no9/201409/t20140911_501474.html